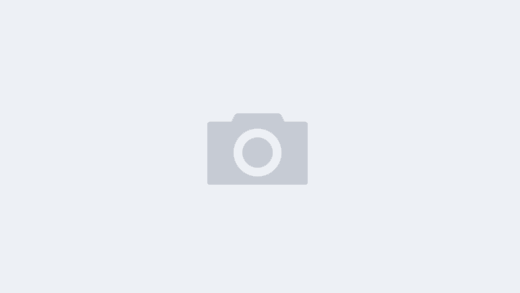不知过了多久,也许是他们觉得今晚的“娱乐”已经足够,也许是终于厌倦了我这块“不开窍的木头”。宿舍里重新陷入了一种带着余韵的、令人窒息的沉默。只有窗外远处偶尔传来的车声,单调地碾过死寂的夜。
眼泪还在不受控制地流淌,滑过太阳穴,没入鬓角,带来一片冰凉湿腻。枕头湿了一大片,紧紧贴着我的脸,又冷又黏。喉咙里堵着一团硬块,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每一次呼吸都牵扯着胸腔深处撕裂般的疼痛。我像一具被掏空的躯壳,瘫在冰冷潮湿的床上,连动一下手指的力气都没有了。黑暗像沉重的铅块,一层层压下来,压得人透不过气,整个世界只剩下无边无际的绝望和冰冷。
就在我几乎要被这绝望彻底吞噬的时候,一种极其轻微的、布料摩擦的声音,在我头顶上方响起。
声音很轻,带着小心翼翼的试探,在死寂的夜里却清晰得如同惊雷。
我全身的肌肉瞬间绷紧,像受惊的刺猬竖起了所有的尖刺。陈锋?王胖子?他们又想干什么?是不是又要扔什么东西下来?是不是觉得刚才的“效果”还不够?恐惧像冰冷的藤蔓瞬间缠紧了心脏。
然而,预想中的嘲讽或投掷物并没有降临。
一只手臂,从我的上铺边缘,无声地、缓慢地垂了下来。
动作很轻,带着明显的迟疑和犹豫,仿佛怕惊扰到什么。
那只手悬停在我床铺上方不到半尺的空气中。借着窗外极其微弱的路灯光,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属于男性的手的轮廓。那手算不上宽厚,指节分明,此刻却微微蜷曲着,透着一股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