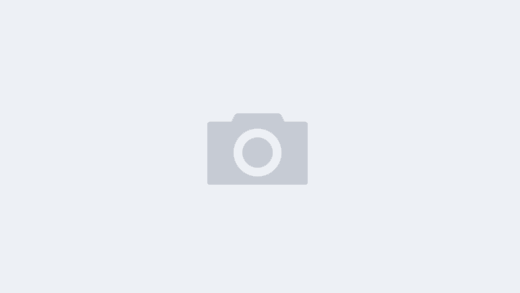然后,我看到那只手的手指间,捏着半包东西。
是纸巾。那种最常见的、包装简陋的白色小包纸巾。半包,被捏得有些发皱。
那只手又往前递了递,距离我更近了,几乎要碰到我蒙在头上的被子边缘。手臂的主人依旧沉默着,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只有那只悬停的手,在极其微弱的光线下,可以清晰地看到——它在抖。
不是轻微的发颤,而是带着一种明显的、难以抑制的抖动。像寒风中一片脆弱的叶子。那细微的震颤,在凝固的黑暗里被无限放大。
一个声音,终于从我的上铺传来。声音压得极低,沙哑,干涩,像是许久没有开口说话,又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喉咙。那声音里,听不出任何情绪,没有同情,没有安慰,甚至没有一丝温度,只有一种近乎僵硬的陈述,带着一种连说话人自己都未曾察觉的紧绷:
“……喂。”
极其短暂的停顿,仿佛在下一个字上耗费了巨大的力气。
“……擦擦吧。”
“喂……擦擦吧。”
那三个字,像三颗裹着冰碴的石子,从头顶上方滚落下来,砸在我蒙着被子的头上,带着一种生硬的、几乎算得上冷漠的腔调。没有称呼,没有温度,甚至没有一丝多余的停顿。然而,那只悬停在黑暗里、捏着半包纸巾、控制不住微微发抖的手,却像一道无声的惊雷,劈开了我眼前浓稠得化不开的绝望。
擦擦?擦什么?擦眼泪?还是擦掉我这身让他们觉得恶心的“脏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