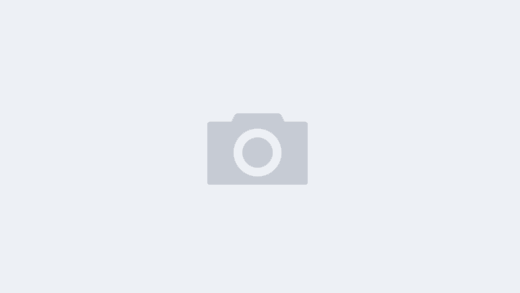巨大的荒谬感和一种被更深层羞辱的愤怒瞬间攫住了我。身体比意识更快地做出了反应——我猛地往里一缩,像躲避什么致命的东西,整个后背重重地撞在冰冷的墙壁上,发出一声沉闷的撞击声。被子被我扯得更紧,死死地裹住头脸,仿佛那半包纸巾是某种剧毒的诱饵。
那只手,在我退缩的瞬间,也触电般地往回一缩,动作快得带起一丝微弱的风声。纸巾包装发出细碎的窸窣声。它并没有立刻收回去,而是再次僵在半空,距离我的床铺边缘更远了一些,只有那只捏着纸巾的手,在黑暗中颤抖的幅度似乎更大了。那细微的震颤,在死寂的夜里,清晰地传递着某种无声的、激烈的挣扎。
上铺的人没有再说话。只有一道压抑得极深、几乎听不见的呼吸声,从上方传来,带着一种奇怪的紊乱节奏。
时间在黑暗里无声地流淌,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宿舍里其他人的鼾声此起彼伏,陈锋那边甚至传来一声含糊的梦呓。窗外的路灯透进来的那点微光,在地板上勾勒出模糊的窗格影子。
那只手,那只捏着半包纸巾、依旧在微微发抖的手,仿佛终于耗尽了所有勇气和力气,极其缓慢地、带着一种近乎颓然的放弃,一点一点地向上缩了回去。动作很轻,像是怕惊扰了谁,又像是怕被谁发现。
纸巾包装的窸窣声再次响起,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