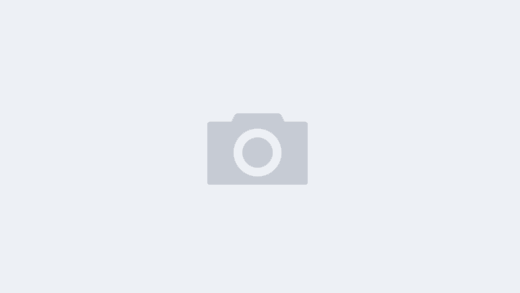我死死地盯着那包纸巾。它静静地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皱巴巴的白色包装在窗外透进来的微光里,像一小片卑微的、随时会被黑暗吞噬的雪。
他扔下来的?还是……不小心掉落的?
心脏在胸腔里狂跳,撞击着肋骨,每一次跳动都牵扯着一种尖锐的酸涩。刚才指尖相触时那冰冷的颤抖感,还在皮肤下顽固地残留着,像一道无法愈合的微小伤口。那颤抖,是因为极度的厌恶和急于摆脱,还是因为别的、更复杂的东西?他最后那声仓促压抑的吸气,是恐惧吗?恐惧什么?恐惧被人看到?恐惧和我这个“死玻璃”有哪怕一丝一毫的接触?
无数个问题在脑子里疯狂冲撞,却找不到出口。冰冷的绝望感并没有因为这包纸巾的出现而消散分毫,反而像沉船后涌上的冰冷海水,更加沉重地挤压着肺腑。这半包纸巾算什么?廉价的施舍?虚伪的怜悯?还是仅仅是一次无措的、仓促的、连他自己都后悔的失误?它甚至不如陈锋他们赤裸裸的恶意来得痛快。
屈辱感像冰冷的藤蔓,再次缠绕上来,越收越紧。我猛地闭上眼,把脸更深地埋进潮湿冰冷的枕头里。身体因为强忍着某种激烈的情绪而微微发抖。别碰它。我在心里对自己嘶吼。别碰!那只会是又一次自取其辱!让它烂在那里!
然而,脸颊下枕头湿冷的触感,鬓角未干的泪痕带来的冰凉粘腻,都在疯狂地提醒着我此刻的狼狈。身体像有自己的意志,在极度的疲惫和混乱中,渴望着一点点的、哪怕是最卑微的干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