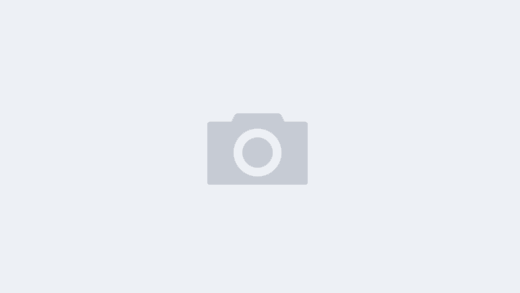我和大军在修车厂拧了五年螺丝,从没觉得哪里不对。
直到那天他递扳手时,指尖擦过我手背的机油。
火花顺着脊椎炸开的瞬间,工具箱哐当砸地。
生锈的卷帘门突然卡住,夕阳把我们的影子钉在满地零件上。
他喉结滚动着蹲下去捡工具,后颈的汗珠滚进工装领口。
“今晚…加个班?”
扳手在我掌心发烫,空气里弥漫着汽油和心跳的味道。
油腻的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汽油味,混杂着橡胶轮胎老化后特有的微甜气息,还有永远无法彻底清除的机油沉淀下来的那股厚重、沉闷的味道。日光灯管在头顶嗡嗡作响,光线是那种惨淡的白色,勉强照亮了这间巨大而杂乱的厂房。金属撞击的叮当声、气动扳手的嘶嘶咆哮、偶尔夹杂几句粗野的吆喝,这些声音构成一种永不停歇的、令人麻木的背景噪音,填满了每一个角落。
我和大军,就像这座钢铁丛林里两枚沉默运转的齿轮。五年了,从初来时手忙脚乱、被师傅骂得狗血淋头的学徒,到如今各自能独当一面,汗水、机油和无数个加班的长夜,早已把我们牢牢地焊接在了这片水泥地上。日子就像重复拧紧同一颗生锈的螺栓,枯燥,但有种令人安心的惯性。
此刻,我正仰面躺在一辆老捷达的底盘下,视线里是锈迹斑斑的排气管和纠缠不清的线路。底盘油泥特有的腥味直冲鼻腔。我费力地伸着手,摸索着那个卡在犄角旮旯里的变速箱滤芯,胳膊肘蹭在冰冷的车架上,留下一道道黑印。
“刘鑫!扳手!快点!”大军的声音从车头方向传来,闷闷的,带着点不耐烦的粗粝,像砂纸刮过金属。
我努力歪过头,视线艰难地穿过底盘复杂的构件,只能看到他沾满油污的深蓝色工装裤裤腿和那双同样油腻不堪、鞋头微微开胶的劳保鞋。他正弯腰在发动机舱里捣鼓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