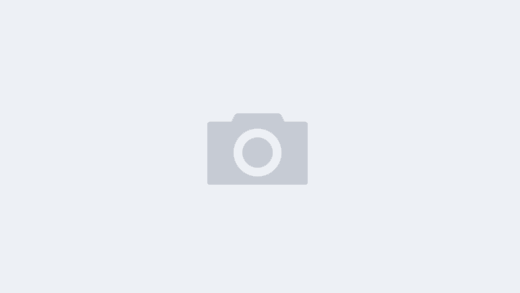照片的碎片像不祥的白色纸钱,散落在我脚边冰冷的水泥地上。陈锋那带着浓重痰音的、心满意足的笑声还在宿舍里回荡,撞击着墙壁,也撞击着我嗡嗡作响的耳膜。他随手拍掉手上的碎屑,仿佛掸掉什么恶心的脏东西,然后一脚踢开那些残骸,像踢开一堆垃圾。他不再看我,仿佛多看一秒都会脏了他的眼睛,转身一屁股坐回自己的床上,掏出手机,屏幕的冷光映着他那张依旧带着亢奋余韵的脸。
宿舍里其他人,也像是被按下了重启键。短暂的死寂过后,低低的议论声、含义不明的嗤笑声、拖动椅子的声音重新响起。但气氛彻底变了。空气里漂浮着一种无形的、粘稠的隔膜,而我,被牢牢地隔绝在这层膜的外面,成了那唯一的、被标注出来的“异类”。那些或好奇、或鄙夷、或避之不及的目光,像无数根细密的针,扎在我暴露在外的皮肤上。我站在原地,脚像生了根,动弹不得。地上那些白色的碎片,刺得我眼睛生疼。弯腰去捡?在众目睽睽之下?那无异于再次把脸伸过去让人践踏。
最终,我几乎是同手同脚地挪回了自己的床铺边,动作僵硬得像一具提线木偶。后背紧紧抵着冰凉的铁架床柱,那点冰冷的触感是唯一能让我确认自己还没有彻底溶解的东西。我把脸深深埋进手掌里,掌心传来一片湿冷的汗意。身体里翻江倒海,胃部一阵阵抽搐,恶心得想吐。下午输球带来的压抑气氛,似乎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娱乐”而消散了不少,至少对其他人来说是这样。他们谈论游戏的声音,谈论晚饭的声音,恢复了某种“正常”。只有我,像被扔进了另一个维度的冰窟里,所有的声音都隔着厚厚的冰层,模糊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