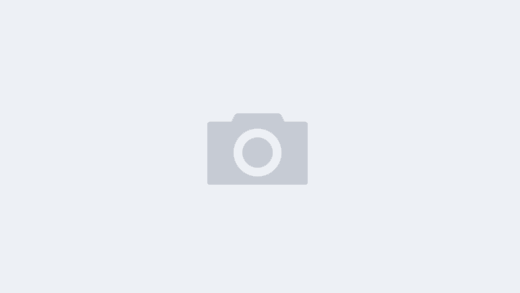“操!”大军低低地咒骂了一声,声音像是从紧咬的牙关里硬挤出来的,带着一种被烫伤的惊怒和一种更深的、我无法理解的慌乱。他的视线飞快地从地上躺着的扳手扫到我的脸,眼神锐利得像刀子刮过,混杂着惊愕、困惑,还有一丝……狼狈?
“搞什么名堂!”他猛地吼了出来,声音比平时拔高了八度,在突然显得过分安静的车间里显得格外突兀,甚至有点失真。吼声像一块沉重的石头砸进死水,激起一圈圈看不见的涟漪。远处几个正埋头干活的工友闻声诧异地抬起头,朝我们这边投来几道混杂着好奇和看热闹的目光。
我张了张嘴,喉咙像是被滚烫的机油堵住了,又干又涩,发不出任何声音。心脏在胸腔里疯狂地擂鼓,咚咚咚,震得耳膜生疼。脸颊火烧火燎,仿佛被车库里那个大功率烤漆灯近距离炙烤着。我慌乱地移开视线,不敢再看他的眼睛,更不敢看那只手,目光无处安放,最终只能死死地钉在水泥地上那个被扳手砸出的、极其细微的白点上。
“我……手滑了。” 终于,几个破碎的音节艰难地挤了出来,干巴巴的,毫无说服力。
大军没再说话。他绷着脸,嘴唇抿成一条冷硬的直线。他不再看我,猛地弯下腰,动作幅度大得有些粗暴。他一把抓起地上那把“惹祸”的扳手,金属与水泥再次发出短促刺耳的摩擦声。他重新俯身,几乎是把自己砸回了发动机舱深处,只留给我一个绷紧的、拒人千里的后背。他拧螺丝的力道大得惊人,扳手与螺帽咬合发出尖锐刺耳的“吱嘎”声,像是在发泄着无处可去的怒火,又像是在徒劳地对抗着什么无形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