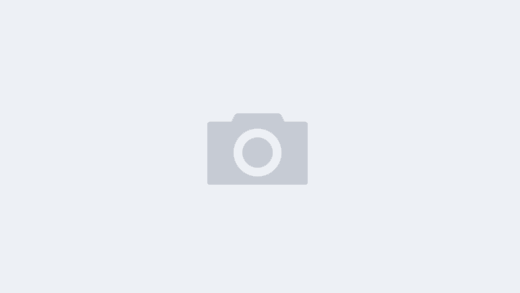“妈的!”大军低骂了一声,带着挫败的烦躁。他用力又拧了几下钥匙,锁芯发出徒劳的呻吟。他抬起脚,泄愤似的朝着那扇顽固的铁门踹了一脚。
“哐——!”一声巨响在寂静的车间里炸开,震得人耳膜发麻。
铁门纹丝不动。
他喘着粗气,肩膀起伏着,背对着我站在那扇卡死的卷帘门前,像一个对着风车宣战的堂吉诃德,徒劳而愤怒。昏黄的灯光从上方落下来,照亮了他后颈上再次渗出的细密汗珠,也照亮了那扇门投下的、巨大而扭曲的阴影,将他整个人都笼罩了进去。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那绷紧的后背,看着那道顽固的缝隙,看着我们被灯光拉长的、在冰冷水泥地上微微晃动的影子。一种奇异的冲动毫无征兆地攫住了我。也许是那声泄愤的巨响,也许是那扇卡死的门所象征的某种徒劳,也许仅仅是这漫长而混乱一天积压下来的疲惫和混乱找到了一个出口。
我向前走了几步,靠近他,停在他身后半臂的距离。空气里他的气息更加清晰了。
然后,我抬起手,不是去碰那冰冷的门,也不是去碰他僵硬的肩膀,而是轻轻地,带着一种连我自己都未曾预料到的、近乎本能的安抚意味,落在了他紧握成拳、因用力而指节发白的手背上。
我的指尖,依旧带着无法洗净的机油污迹,触碰到他同样粗糙、布满油垢和汗水的皮肤。
那一瞬间,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扼住了整个空间。车间里所有残留的机器嗡鸣、水管滴答、甚至空气本身的流动,都在这一刻彻底凝固、消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