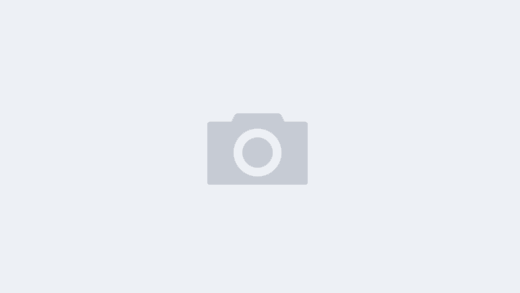一抬头,心脏猛地一缩。
大军就站在几米开外,靠在一辆拆了一半、露出内脏般复杂管线的面包车车头上。他没看我,侧着脸,目光投向那扇巨大的、布满铁锈的卷帘门,夕阳的金红色余晖勾勒出他硬朗而沉默的轮廓,鼻梁挺直,下颌线绷得很紧。他指间夹着一根刚点燃的烟,烟雾袅袅升起,在昏黄的光线里扭曲变幻。那一点暗红的火星,在他沾满油污的手指间明灭不定,像他此刻难以捉摸的情绪。
我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手脚又开始僵硬。空气里弥漫着劣质烟草辛辣的味道,混合着未散的机油和汽油气息,沉甸甸地压在胸口。我犹豫着,是像耗子一样溜走,还是……打个招呼?喉咙发紧。
就在我踌躇不决时,大军似乎终于抽完了那根烟。他狠狠吸了最后一口,把烟蒂扔在地上,用他那厚重的劳保鞋底用力碾灭。然后,他抬起头,目光像探照灯一样,毫无预兆地、直直地朝我扫了过来。
那眼神复杂得像一团纠缠的旧电线。有未消的余怒,像闷燃的火炭;有深不见底的困惑,仿佛被困在迷宫里找不到出路;还有一种更沉重的东西,或许是不安,或许是别的什么,沉甸甸地压在眼底。夕阳的金光落在他眼睛里,却奇异地没有带来丝毫暖意,反而像淬了冰。
我们隔着几米远的距离,中间是散落的轮胎、废弃的零件和那道斜长的橘红色光带。空气凝固了,只有远处水管偶尔滴水的“嗒…嗒…”声,清晰得如同敲在紧绷的鼓面上。我能清晰地听到自己擂鼓般的心跳,一下,又一下,沉重地撞击着肋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