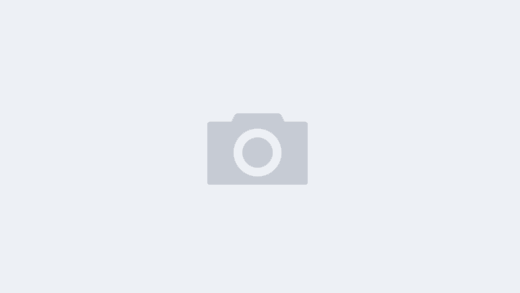空气里弥漫着无声的张力,比任何机器的轰鸣都更令人心悸。汽油味、机油味、还有那无处不在的、属于他的汗水和烟草的气息,混合成一种令人眩晕的催化剂。我深吸一口气,那混杂的气味涌入肺腑,带着一种奇异的灼热感。我强迫自己迈开脚步,朝他走去,走向那辆捷达,走向那片由他制造出来的、沉默而滚烫的漩涡中心。每一步,都像踩在无形的钢丝上,摇摇欲坠。
走到升降架旁,浓烈的汽油味扑面而来。大军已经钻到了车底下,只看到他那双沾满油泥的劳保鞋露在外面。工具碰撞的声音开始响起,叮叮当当,比平时更响,也更急躁,像是在发泄着什么。
我蹲下身,拿起一个套筒,递向他露在外面的手边。他摸索着接过去,手指不可避免地再次擦过我的指尖。这一次,我像被烙铁烫到般猛地缩回了手,动作快得有些狼狈。
车底下传来一声压抑的、模糊的闷哼,像是吃痛,又像是别的什么。
沉默。只有扳手拧动螺丝的“吱嘎”声,单调而刺耳地撕扯着寂静。这声音持续了很久,久到我蹲着的双腿开始发麻,久到厂房里最后一丝天光也彻底被黑暗吞噬,只剩下我们头顶一盏昏黄的工作灯,投下两个被拉得巨大而扭曲的影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无声地晃动、纠缠。
突然,“吱嘎”声停了。一片死寂。
我下意识地屏住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