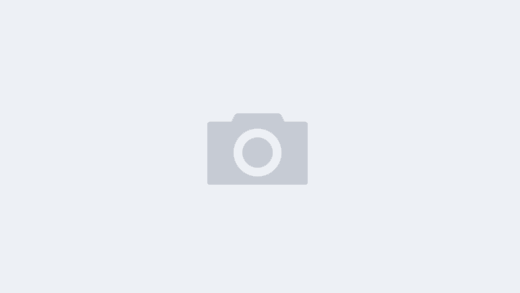大军猛地一僵!像被高压电流瞬间贯穿。他后背的肌肉瞬间绷紧,硬得像一块烧红的铁板。他那只被我触碰的手,下意识地、痉挛般地往回一缩,仿佛我的指尖带着烙铁的温度。
时间被拉长成了粘稠的琥珀。几秒钟?或许更久?只有我们头顶那盏昏黄的工作灯,还在发出稳定而微弱的电流嗡鸣,将我们沉默对峙的身影投射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边缘模糊地纠缠在一起。
他没有立刻甩开。那只被我触碰的手,在最初的剧烈退缩后,僵硬地停在了半途,微微颤抖着。我能清晰地感觉到他皮肤下奔流的血液滚烫的温度,透过油污传递过来。他依旧背对着我,但整个身体都呈现出一种高度戒备的姿态,像一头随时会暴起反击却又被无形绳索捆住的困兽。
空气里,那股浓烈的机油和汽油味似乎被一种更原始、更滚烫的东西蒸腾了起来——汗水的咸腥,还有那种只有极度紧张时才会散发出的、几乎能嗅到的荷尔蒙的气息。我的心跳声再次擂鼓般响起,震得耳膜嗡嗡作响,几乎要盖过灯管的嗡鸣。
他终于,极其缓慢地,转过了身。
动作滞涩,仿佛每一个关节都在抵抗。他面对着我,昏黄的灯光照亮了他的脸。那张棱角分明、沾满油污的脸上,此刻没有下午的惊怒,没有方才的疲惫,只有一种近乎空白的震惊。他的眼睛瞪得很大,瞳孔在灯光下微微收缩,里面清晰地倒映着我同样惊惶失措的脸。那眼神复杂得像一团被彻底搅浑的泥水,惊涛骇浪在其中翻涌、撞击:难以置信的愕然,深不见底的困惑,一种被冒犯的怒意,还有一种更隐秘、更原始的……恐惧?那恐惧并非针对我,更像是对他自己内心某种未知领域的剧烈排斥和惊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