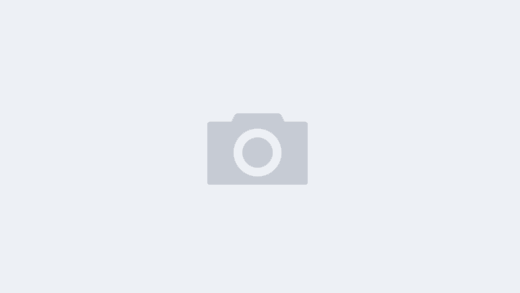这沉默不再仅仅是尴尬或紧张。它像刚刚退潮的沙滩,湿漉漉的,带着被剧烈冲刷后的痕迹,也留下了一些难以言喻的东西。我低头看着自己同样沾满油污的手,下午那触电般的灼热感早已消失,但掌心似乎还残留着某种微妙的麻意。
他洗完手,拿起那块破毛巾,胡乱地擦着脸和脖子,动作依旧粗鲁,但似乎不再那么紧绷了。他把湿漉漉的毛巾扔在一边,然后双手撑着膝盖,有些费力地站了起来。高大的身影挡住了部分灯光,在我身前投下一片更深的阴影。
“走吧。”他说,声音依旧低沉沙哑,但少了刚才那种孤注一掷的紧绷感,多了几分纯粹的疲惫,“……锁门。”
他不再看我,转身径直走向车间尽头那扇巨大的、布满铁锈的卷帘门。钥匙在他手里发出哗啦的轻响。
我默默地跟在他身后几步远的地方。脚步声在空旷巨大的车间里回荡,一前一后,敲打着沉寂。空气里浮动的机油分子和汽油分子似乎也沉淀了下来,只剩下一种沉闷的、带着金属余温的气息,还有他身上那股挥之不去的汗味,混合着刚刚洗过的、冷水的气息。
他走到卷帘门前,弯下腰,将钥匙插进那个同样锈迹斑斑的锁孔。用力转动。
“咔哒…咔哒…吱嘎——!”
刺耳的金属摩擦声猛地响起!卷帘门剧烈地抖动了一下,向下滑落了不到十公分,然后就死死地卡住了,顽固地停在半空中,像一个巨大的、生锈的嘴巴,咧开一道黑黢黢的缝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