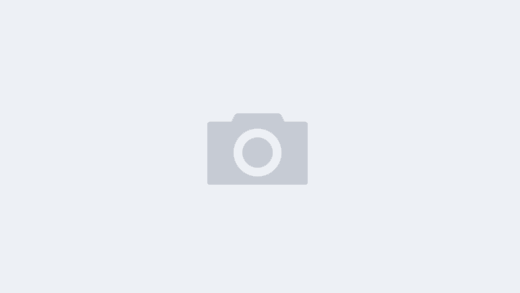陆骁的“凶”气僵在脸上,有点下不来台,又有点莫名的期待。他猜江屿大概会翻个白眼不理他,或者小声嘟囔一句“神经病”然后收拾东西走人。然而,江屿只是翻到了某一页,然后动作停了下来。他伸出修长干净的手指,小心翼翼地将那张纸从本子上撕了下来。
接着,江屿站起身,走到铁丝网前。夕阳的余晖落在他身上,给他周身镀上一层柔和的金边。隔着细密的网格,他把那张撕下来的画纸递了过来。
陆骁下意识地伸手接过。
画纸还带着画板上的微温和铅笔的炭粉气息。
纸上,只有他。
画的是昨天训练间隙,他仰头灌水的瞬间。角度抓得极其刁钻精准。画面上,他仰着头,脖颈拉出一条绷紧而充满力量感的弧线,喉结因为吞咽的动作而异常突出、锋利地滚动着。汗水凝成的水珠正沿着那绷紧的颈侧皮肤,一路滑落,清晰得仿佛下一秒就要滴下来。几缕湿透的刘海黏在饱满的额角,眉宇间带着运动后的疲惫和一种近乎兽性的专注。
没有背景,没有球场,只有他喉结滚动的那个充满原始张力的瞬间。
陆骁的呼吸猛地一窒,像是被人扼住了喉咙。一股滚烫的热流“轰”地一下从脚底板直冲头顶,烧得他耳膜嗡嗡作响,脸颊烫得能煎鸡蛋。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那颗心在胸腔里疯狂地擂动,撞击着肋骨,发出沉重的“咚咚”声,震得他手指都微微发麻。他死死地盯着画纸上那个被无限放大、被赤裸裸呈现的喉结,仿佛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见”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以一种全然陌生的、极具侵略性的美感。